走进时光的叠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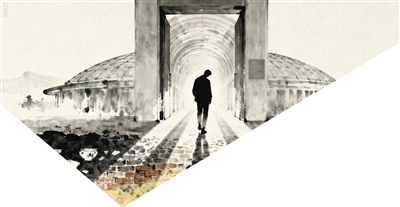

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早已不再是行走的全部。
一座正在举办考古成果展的城市,就像一个有故事的人,从容、厚重,充满了让人不断探寻的魅力。

鲁公桥遗址:
土台上的地层密码
国庆长假临近,若你来杭州,临安博物馆正展出的“发现杭州——2024年度杭州考古成果展”,是这座城市最新亮相的时光窗口之一。274件(组)最新被发掘的文物、22个横跨史前至明清的考古项目,共同搭起了“发现杭州”的记忆剧场。
这“记忆剧场”的故事之所以迷人,也许是因为每一件文物都牵连着城市的过往:淡蓝色的琉璃小瓶,似从丝绸之路的驼铃声中走来,是城市对外交流的一枚印章;橘红的玛瑙珠里,映衬着古人举手投足间的恬淡;狰狞又威严的兽首构件,曾在古建筑上镇守一方,是城市形成之初的“图腾”……
在“发现杭州”展厅,最先吸引观众目光的,是两处形态各异的沙池。其中一处,还原了萧山鲁公桥遗址9000平方米的发掘区,淡黄色的沙土代表良渚文化地层,深褐色对应宋代堆积,黑色则是明清遗存。
沙池里插着细小的标识牌,标注着“陶过滤器出土点”“堰坝遗迹”“墓葬群”,那些张晓坤和团队成员曾蹲在泥水里清理的遗迹,如今以立体的方式呈现在公众面前。“之前总听人说‘地层叠压’,今天一看沙池,才明白不同年代的历史是怎么‘叠’在一起的。”一位观众在旁感叹道。
张晓坤,1996年出生,厦门大学文物与博物馆专业(考古方向)研究生。鲁公桥遗址是她担任现场负责人的第一个大遗址,也是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2024年发掘的项目中面积最大、时间最长的遗址。作为2024年度浙江考古十大重大发现之一,杭州萧山鲁公桥遗址共清理出从良渚文化时期至明清时期的各类遗迹260余处,其中尤以良渚文化时期的发现最为重要。
都说考古人的工作是破译无字地书,草木灰、夯土、路土、粉灰土……探方四壁的剖面像是一本被反复批注的书,印着各时代的指纹。
张晓坤记得,2024年梅雨季,连续半个月的暴雨让鲁公桥遗址发掘区变成池塘,有天早上,整个探方四壁下坍塌的土变成了淤泥,之前画的地层线全没了。
“良渚时期也会有这样的天气,雨后地层里可能留一层沙土,晴天人们扔的垃圾,又会形成有机质的腐烂——这些沙土都是有迷惑性的,是历史的‘尘埃’。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去伪存真,除了观察确认土质土色包含物,也要根据出土器物的年代做相应辨别。”张晓坤说。
在鲁公桥遗址,张晓坤和她的团队发掘到一处遗迹,地层剖面上是凸起的土堆,土堆以北可见水流作用形成的地层,土堆以南又是一处低凹地。这是生活台地还是其他遗迹?最终确认,这是一处堰坝,曾经历过三次洪水期。每一层淤积里,都藏着良渚先民与自然共生的智慧。
这样的时刻,总不免会感慨,古人所亲历的沧海桑田,是真真切切刻在文明脉络里的过往,是他们用一生丈量的时空、用足迹踏过的变迁,从无半分“虚度”。
我们又何其幸运:相较于困于时代局限、难以行进远方的古人,我们不仅能循着考古线索回望他们生活的世界,更有机会触碰藏在未来的无限可能。
文明的传承,是你我他,都成了历史的“参与者”。

衣锦城遗址:
山水间的筑城典范
若说鲁公桥遗址藏着先民的生活智慧,那要读懂城市的生长脉络,便不能不追问“人们为何筑城”——在人与土地的羁绊里,每一座城都有专属的成长密码。
在“发现杭州”,另一处别有洞天的沙池用光影还原了衣锦城遗址的样貌,灰色的沙粒堆出东城墙的轮廓,圆弧形的东南城隅清晰可见,细小的蓝色砂砾模拟出锦溪与苕溪的走向,沿着城墙内侧延伸的“排水沟”,正是刘青彬团队2024年底发现青瓷的关键区域。
2024年12月,刘青彬来到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报到,他的专业特长是对史前时代的考古挖掘。而浙江坐拥上山文化到良渚文明的丰富史前资源,史前考古本就是浙江考古的重中之重。
此前,刘青彬在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巩义双槐树遗址(新石器时代都邑性质聚落)的调查与发掘,他都在场。
从中原到江南,刘青彬来不及在杭州市区停留,便直奔临安衣锦城遗址现场。衣锦城,最初只是军事用房,后来逐步发展为衣锦营、衣锦城。而最让刘青彬觉得有趣的发现,是东南城隅的圆弧形拐角——“这是古人的前瞻性,考虑到了防洪需求。”
研究衣锦城时,刘青彬总忍不住将其与郑州商城对比:郑州商城是商代早期的都城,建在平原上,虽依傍水系,但主要依托平原地形,且夯土技术高超,数千年后核心部分仍坚固屹立;而衣锦城是“山水城合一”的典范——北墙沿太庙山脊修建,既可凭高防守,又能守卫钱王陵,且四面环水,锦溪、苕溪环绕,将自然环境与城市建设完美融合。这种南北差异,恰是不同地域文化特色与生存智慧的写照。
在衣锦城遗址的工棚里,入口处显眼地挂着《咸淳临安志》收录的《临安县境图》,这是刘青彬目之所及“最远”的风景。工作间隙,他爱对着地图琢磨:沿锦溪与苕溪的水脉溯流西北、顺行东南;停在太庙山望向功臣塔的飞檐时,他会猜想:那道隐没在现代建筑群中的虚实轴线,是否正是钱镠 “衣锦还乡” 时,车马仪仗踏过的城市中轴线?
从郑州商城的平原筑城,到衣锦城的山水相依,地域不同、文化各异,但古人筑城求安、向美而生的初心不变。
2025年3月,杭州临安衣锦城城墙遗址与萧山鲁公桥遗址,一同入选2024年度浙江考古十大重大发现——这是对两处遗址价值的认可,更是对考古人付出的回应。

玉架山考古博物馆:
用身体阅读的考古报告
考古是与时间拔河,考古成果展是考古人躬身求索后交出的“文明结晶”,而博物馆则是给时间穿针引线的“摆渡人”——它让历史走出探方,走进人们的生活。
在近年来迭起的博物馆热潮中,殷墟遗址博物馆、晋阳古城考古博物馆、苏州考古博物馆等相继开放,考古遗址博物馆正成为新兴的文化坐标。
与传统综合性博物馆不同,这类博物馆里,或许没有被观众围堵打卡的“国宝”,但沉睡千年的墓葬形制、夯土基址、建筑群落遗址,以及考古学科的讲述逻辑,才是真正的核心展品。
玉架山考古博物馆是浙江省第一座考古博物馆。馆长吕芹与杭州文博事业的缘分,要从2004年说起。那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硕士毕业的她,背着行囊来到杭州,考入余杭博物馆,此后从余杭博物馆到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再到海塘博物馆,如今执掌玉架山考古博物馆——她的工作轨迹,恰是一条串联杭州文化记忆的丝线。
在玉架山考古博物馆,展陈上标注着考古编号,多媒体屏幕提供石器材质数量表、漆器墓葬位置检索,甚至在抽屉里陈列不同硬度的玉料标本……用考古学的方法解读历史,是为了把更多的可能性留给观众。
“2003年底,我准备报考余杭博物馆前,先去了馆里参观。那时候馆里就做了场景复原,一条老街还原出江南水乡的烟火气,让我有了‘我打江南走过’的对话感。”也正是从那一瞬间起,让吕芹意识到,如何让博物馆的展陈从“以物为导向”转向“以人为导向”,如何让观众感受到这是一座“会呼吸、有记忆”的博物馆,才是博物馆发展的方向。
在玉架山考古博物馆的中心,一面近乎四层楼高的落地玻璃幕墙如一面瀑布,一窗之隔,玉架山考古遗址公园的天光与云影倾泻而入。幕墙顶端,挂着一支斑驳的船桨,像是表盘的指针,来来往往的人经过这儿,总会停驻片刻,但更让参观者流连的是考古博物馆沉浸式的展陈设计与近在咫尺的观展模式。
当观众踩过考古探方的玻璃栈道,透过保护罩凝望叠压的城墙遗迹,不同朝代的夯土层宛如大地书写的编年体史书。置身其中,像身处一座有回声的剧场,离历史更近了。
但是,这一切还不是让吕芹最为自豪的。
吕芹把原本计划做成数字展厅的空间腾让出来,做成了无障碍展厅。“我在想,做博物馆不一定要做多大、多有影响力的事情,要做一些小事,方方面面的细节都考虑进去,就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为了做好这件事,吕芹专程去北京参观了视障文化博物馆,体验了“黑房子”——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环境中感受视障人群的处境。“那种对前方未知的恐惧感,我至今难忘。回来后我就想,这个无障碍展厅一定要落地,一定要做好。”
在玉架山考古博物馆的无障碍展厅,观众可沿着盲道前行,每一个点位都有盲文解说牌。墙面嵌入可触摸的玉架山聚落模型——凸起的土丘代表祭坛,凹陷的沟壑象征护城河,而一粒粒的线暗示是洪水痕迹;在时长近7分钟的声音剧场,听得见良渚时期的夯土声、陶器轮制声、火柴燃烧声、房屋倒塌声……这是用身体阅读的考古报告,听觉已成为解读遗址的新维度,每个与文明对话的瞬间,都是正在形成的历史。
这个长假,你的旅行清单里有博物馆吗?待假期落幕,我们重新投入生活的琐碎与忙碌,那些从历史中拾起的感动、沉淀的思考,早已化作心底的笃定。因为我们知道,在这片土地上,有无数人在默默守护着文明的火种,而这些跨越千年的智慧与力量,终将成为每个人前行路上的底气。它们曾属于过往,现在亦与我们息息相关。